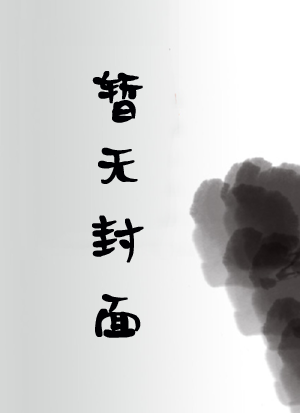第一卷:默認 第904章 到底到底
耳鳴還在回旋,他什麼也聽不到。
身體好像變得不是自己的了。
他眼前全是散亂的光,可他還是一點點轉過頭,看向了副駕的方向。
前面的車窗開裂了,但并沒有玻璃濺出。
葉空……葉空很安全。
她隻是呆呆地坐在那裡,在這場擦肩而過的緩緩消散的死亡中一動不動,像是被吓呆了。
——
這片刻之後,他的大腦才算能重新運轉起來。
在長長的耳鳴裡,他這才緩緩看向自己的手。
死死掰着方向盤,仿佛生怕有一點松懈,以一個想放松也無法做到的姿勢僵滞地握着,手指用力到指甲撕裂滲出血來,每一根都在痙攣。
他無聲的,空白的看了很久,好像才終于漸漸意識到發生了什麼。
他慢慢松開方向盤,仰頭靠在椅背上,急促的喘息,像個瀕死的病人。
眩暈中他恍惚在殘存的夜色裡看見了池彎刀的臉。
他脫力地坐在這輛車裡,又好像坐在了七年前那個無能為力的副駕駛上。
他看見池彎刀在那個刹那到來時神從天降般猛地轉動方向盤的手。
他看見她在朝他挑眉,好像在說“我就知道”。
他看見火焰散去——這麼多年,那永恒燃燒着的駕駛座上的火焰終于第一次散去,他也第一次看見了那颠倒的車上,颠倒的池彎刀對窗外的他露出的最後一個表情。
——不是痛苦的吼叫,不是怨恨的哭泣,甚至不是掙紮與歎息。
她隻是在笑。
她在對他微笑,一如從前的每一天,每一次。
“檢測到車身發生劇烈碰撞,現在打開安全氣囊——”
經過改裝的,一往無前為死而生的跑車上是沒有安全氣囊的。
人工智障操着池彎刀的聲音,嘩嘩打開了跑車的敞篷模式。
夜風與整個世界呼呼湧入車廂,吹醒了渾身僵直不動的葉空。
她仿佛陷入一場世界颠倒的幻夢,至今也未能清醒,腦袋一點點轉過來的時候眼瞳也還是凝結的。
當敞篷完全打開的時候,風聲一下變得巨大,發出嘩啦啦如海浪潮湧的聲音。
然後一本輕盈的小冊子輕盈地翻飛起來,啪的一聲如雪白的飛鳥般撞在了前面的車窗上。
接着是第二本、第三本……不死妖的《銀河之花》、《沙之書》,連同大部頭裡壓着的池彎刀那些寫着密密麻麻公式的草稿……它們從跑車的後座上被風卷起,呼啦一聲向着夜色向着高空漫天翻湧,似吹開一朵陡然怒綻的巨大的花,也如一場毫無預兆鋪天蓋地的雪。
葉空漆黑的瞳映着這場白色的雪,也映着翻飛的書頁間靠着椅背擡手捂住臉的溫璨。
他在呼啦啦的風聲裡突然笑了起來。
笑聲從指縫間流出,含着顫抖的鼻音,一點點變大,卻逐漸叫人分不清到底是在笑還是在哭。
葉空也在顫抖。
她的大腦好像也經曆了一場宇宙大爆炸,心髒還在顫動,靈魂還沒有歸位,戰栗卻悄無聲息的布滿了每一寸皮膚。
在真正意識到發生了什麼,這一切代表了什麼之前,一個念頭先浮現在她的身體裡。
那是先于理智,先于大腦,先于任何能思考的神經所發出的,猶如來自靈魂深處本能地問題。
她看着緩緩停止大笑或大哭,緩緩彎下腰去撿那把手槍的溫璨,呆呆地想——
到底何以為愛呢?
·
溫璨用了三次才撿起那把槍。
他打開車門,在近在咫尺的山壁前勉強推開一條縫鑽了出去,然後踉踉跄跄走向不遠處那輛黑色轎車。
它就懸停在懸崖邊上,撞壞了一路的欄杆,拖出了一地的胎痕,卻最終沒有沖出去。
真是好命啊。
溫璨心想。
他的大腦還在眩暈。
所有想法和感受都如同隔了層玻璃般麻木,于是眼神也漆黑遲滞,沒有一絲情緒。
他隻是頭重腳輕地走向那個從轎車裡爬出來的人。
他渾身都在篩糠般的抖,他趴在地上一邊嗚嗚哭泣着一邊看向四周,仿佛還在找那個不存在的“惡鬼”。
可他看見了行走的人。
他從那輛跑車裡走下來,走過這條無盡的公路,走過漫長的七年,走過那場爆炸和死亡,來到他面前,對他舉起了黑色的深淵般的槍口——
“不!!!”
溫榮終于清醒過來,他勉強意識到這不是惡鬼不是亡靈,而是活生生的他的兒子。
想要殺死他的他的兒子!
槍口如此冰冷地抵住他的額頭,死亡逼退了不遠處的黎明,成為倒轉的夜和漆黑的山,鋪天蓋地地壓在他頭上肩上,要将他拖入永不見底的沼澤裡。
“不要!”
眼淚像奔騰的海從他難看的渾濁的眼睛裡滾出來。
他猛地一下跪在了地上,佝偻着幹瘦的身軀,抓住了溫璨的褲腳。
他五指像白骨一樣痙攣地抓着溫璨,發出了可憐的嚎啕:“求你!求你了!不要殺了我!我錯了!阿璨!我錯了!我不該殺了你媽媽不該殺了你!我鬼迷心竅,我不是人!”
他直起身來,猛地一巴掌呼在自己臉上,那張總是溫文爾雅佯裝仁慈的臉上涕泗橫流,同時又填滿了一本正經的極端的憤怒和恨恨,他像對待仇人一樣咬牙切齒地打自己的臉,每打一下就惡狠狠唾罵一聲:“我是畜牲!我是個賤人!我該死!我是個混蛋!我不配活着!全都是我的錯!我會下地獄的!我是個禽獸!!我肮髒我卑賤!我就是個不配為人的垃圾!我是豬我是狗!我該死!我真該死!”
……
凹陷下去的臉幾下就變得又紅又腫,很快又開始淤青滲血,最後高高的膨脹起來,已經完全面目全非得看不清五官了。
這樣一張生動的、惡心的、肮髒的臉,就這麼映在溫璨一動不動鏡子般的眼睛裡。
懸崖之外,遠天裡一點模糊的金色欲要噴薄而出。
這條公路上,槍口卻帶着冰冷夜色特有的溫度不為所動地抵着溫榮的額頭。
他被徹底壓垮的心終于再也支撐不住,粉碎的軀殼裡袒露出懦弱惡臭的靈魂,那靈魂發出歇斯底裡的可憐嚎啕來。
腫脹的眼睛裡擠出肮髒的眼淚,把那張本就豬一樣猙獰變形的臉洗得更加肮髒了。
他發出待宰牲口般慘烈的嚎叫,整個身體都五體投地趴在地上,和眼淚一起流出來的,還有褲子上漸漸濕潤的水迹。
他哆哆嗦嗦地尿出來了。
他遲鈍地感覺到了,屈辱地擡手擋住面孔,又渾渾噩噩極傷心的嗚嗚哭起來,哆哆嗦嗦念着:“求你,求你了兒子……不,我是你兒子,我求你了,阿璨,你是我爹,你是我爺爺,别殺我,别殺我,我會去乖乖坐牢的,我會自首的,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我害怕……我害怕……嗚嗚嗚嗚……我是你爸爸啊……嗚嗚嗚……”
溫璨死寂的鏡子般的眼睛裡泛起一點笑來。
那笑像冰涼的薄雪一般落下,漸漸覆蓋了這整個荒誕的滑稽的世界。
在他身後,葉空打開車門下來了。
她站在跑車邊,站在嘩啦啦翻卷的書頁中,看着那一站一趴的兩道影子,聽見風送來的絮絮叨叨的求饒。
在那一聲聲癫狂的“你是我爹”、“我不想死”,以及溫榮猛地開始磕頭的砰砰悶響裡,她又怔怔的想——
她想,到底何以為人呢?
風吹着男人皺巴巴的襯衫和長褲,勾勒他瘦而長的影子。
短發在風中亂飛,露出深暗寂靜的眼睛。
他握着槍,看着跪在地上的人突然轉身想要逃跑。
他早就沒了體力,又被恐懼擊垮了全部的精神,隻能用怕死的卑賤的靈魂拖着沉重的軀殼一點點往遠離死神的方向爬去。
褲子上的水在地面拖出蜿蜒的濕痕。
他一路哭着,用渾身每一寸皮膚渾渾噩噩地向遠處蹭去——
在這相似的道路上,在這相似的跑車前,溫璨看見了那個同樣趴在地上,卻往相反方向拼盡全力艱難爬行的自己。
他看見他的血和淚,看見他和眼前這道遠去的蠕動的影子重疊,然後交錯,撕裂,背對而行。
二十七歲的溫璨握着槍,擡起頭望着這春夜的天,發出一聲短促的含淚的笑。
然後他低下頭來,收起全部的表情,擡起手臂,用攜着血迹的手指,對着那道污濁般的影子,扣動了扳機——
砰——
砰——
砰——
砰——
四聲槍響穿透長夜,抵達葉空耳邊,也抵達山路之外另外三個人的耳邊。
車廂裡的曲霧和葉亭初猛地坐直身體瞪大了眼睛。
層層盤山路之下某個被改動的路牌邊,正蹲在地上抽煙的穿着外賣制服的費秘書擡起頭,看向了高處黑乎乎的山林。
群鳥驚飛,嘩啦啦散開大片黑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