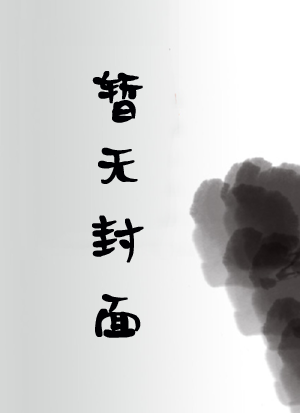第117章 楚楚,我該走了
說完之後,林楚楚也找了個地方坐著,從老頭嘿嘿一笑,「您繼續,繼續……」
老頭嘴角僵硬地扯了扯,拿著增廣賢文繼續。
拉長的語調,黏黏糊糊,課堂裡安靜的放屁都跟雷似的。
二爺講課好似催眠曲,沒多一會林楚楚就開始犯困。
桌子不知道被敲多少回,腦袋小雞吃米似的點著,好容易熬完到了下課,二爺大長臉從胸脯耷拉波靈蓋。
瞅都沒瞅林楚楚一眼,留下作業轉身就走。
林楚楚被他瞪的摸不著頭腦,「錚哥,我又怎麼他了,這老頭瞪***啥?」
拇指若無旁人地在唇角抹了抹,閻永錚捏了捏她肩頭,笑著說:「你流口水了……」
「啊?」林楚楚愣了愣,又嘿嘿地笑了起來。
問了一下跟過來的夥計,不光她沒聽懂,所有人都跟聽天書似的。
「不著急,學堂裡不光他一個夫子。」林楚楚臉上掛著笑,「牆上有現成的千字文,先認一認,屋裡有紙筆能抄幾個是幾個,過兩天再來,別的夫子上課保管比老頭的強。」
家裡那頭,除卻阿緻以外,陳晉元徐文清等人皆是寒著一張臉。
連飯都每吃,直接回了城裡。
一整天都沒看見趙安生的人影。
晚上的時候,阿緻叫住林楚楚道:「楚楚,我該走了。」
「這麼快,不能留下一起過年嗎?」林楚楚詫異.
「一年了,也該回去了。」該面對的總要面對,阿緻笑容有些慘淡,她道:「多謝你救了我,讓我在這裡待了這麼久。」jj.br>
四周的房屋,青山鄉間,一切都那麼熟悉,卻以後不會再來了。
阿緻沒說什麼漂亮的話,簡單的感謝,這些日子的相處,讓林楚楚濕潤了眼眶,「別說些了,當初救你不過是搭把手,以後想這裡了再回來。」
「嗯。」阿緻點了點頭目光瑩潤,看了一眼與自己一樣的硃砂痣,傾身上前抱住了她「楚楚,山高路遠來日方長。」
「嗯,來日方長。」
晚上寂靜村裡上掠起一陣急促馬蹄聲,聲響停下,阿緻披著衣衫等在院前。
高頭大馬上下來個身穿甲胄的男人,那人見了阿緻,不由分說緊緊擁住了她。
凄冷的月光下,大地都照成慘白色。
閻永錚在黑暗裡注視著,「你……」
趙安生垂下頭神色黯然,「時候不早了,我該歇著了。」
他跛腳的身影被拉得老長,寒風吹起衣袂說不出的寂寥。
那人跟阿緻說了好一會話,擦去她臉上的淚,轉身像院裡走去。
瞧清楚來人面容那一刻,院裡院外的兩個人皆愣了一瞬。
官府的車駕第二天早早就到了閻家門口。
家裡人都來送行,卻獨獨少了趙安生。
「阿緻,要是惦念了就託人來信。」林楚楚遞給她一個包裹,「都是些你喜歡的零嘴,留著路上吃。」
「嗯。」收下包裹,阿緻朝著眾人一一點頭,腳步卻沒有動彈。
身後徐文清催促道:「時辰不早了,城裡還有接應的人。」
阿緻喘了幾個呼吸,依舊沒看見那個跛腳的身影,淡然笑了下,走到林楚楚身邊很輕地說,「我姓梁,叫梁緻。」
梁是大昭國姓。
不是大昭皇室,又怎會受陳晉元徐文清如此禮遇。
等林楚楚反應過來的時候人已經上了馬車,走遠了。
車子行駛到村口,馬車上窗戶上的轎簾都沒有放下來,直到出來村子,她才恍然一笑。
在她看不見的地方。
趙安生坡著腳,不顧腿上的疼痛穿行在村路旁的林子裡,簪子在手裡捏出血痕,卻沒敢朝著馬車喊上一聲。
躊躇不敢問初衷。
一切幻夢皆成空。
還未宣之於口的情愫,隱於心口之下,他們都沒有那麼勇敢,沒有人敢踏出第一步。
人在的時候沒覺出什麼。
人一走,林楚楚就覺得好像一根線牽在了心裡,時不時地就能想起她來。
年關將至。
臘月二十三,小年那天第一批毛衣在豫州城亮相。
梭織的針法,v字領,圓領,從未見過的樣式,穿法徹底驚到了豫州城人。
毛衣的售價不便宜,毛衣毛褲要一兩銀子。
可即便是這樣首日掛出來的兩百套,也全都售賣一空。
同一時間,鮮魚鮮的門口擺了貨架,賣老闆娘新研製出來的豆瓣醬。
貨架旁邊支了做菜的鍋,現場炒制放了豆瓣醬的菜。
不同於水煮魚的辛辣味道,頓時吸引住人群。
三十文,還沒有飯館裡一道菜貴,買回家卻能用上好一陣子。
這天光是賣豆瓣醬,林楚楚就凈賺了二十多兩。
與此同時,從徐敏懷哪裡分出來一半毛衣被送往京城。
從未見過如此新奇的穿法。
四隻胳膊身軀包住,貼身穿著暖暖和和,比棉衣大氅簡直不要方便太多。
連宮裡的娘娘們都是人手一件。
「好有那個什麼豆瓣醬。」齊府的管家道:「果酒、烈性米酒,和咱們競爭的白糖都是豫州那邊產出來的,跟這次的毛衣都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不過是些小物件,當不得真。」齊景軒撚著佛祖,「齊家生意好了這麼些年,偶爾漏點湯出來給他們算不得什麼。」
「就怕長此以往,攬月閣把手往江南伸。」管家憂慮說:「下邊人打探出來,姓徐的開始在同州留意商鋪,就是給那兩個泥腿子用的。」
「酒樓小物件這些對咱們齊家來說當然不算什麼,但是二爺。」
那管家伸出兩個手指頭,「攬月閣的商隊隻出關一趟就錚了這個數。」
說到了這,齊景軒才掀開了眼皮,「二十萬兩,這倒是令人意外了。」
緊接著他抿唇笑笑,「給胡勛去封信吧,這些年的銀子不能白送,他也該動一動了。」
「再有二爺,安陽王府那位回來了。」
「誰?」齊景軒凜眉佛祖收了起來。
「長玥郡主,老奴也納悶呢。」管家道:「之前不是說死了嗎?怎麼突然就詐屍了。」
「回來了好啊!」齊景軒笑笑,眼中儘是化不開的陰鷙,「她不回來,京城這盤棋可就沒意思了。」
另一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