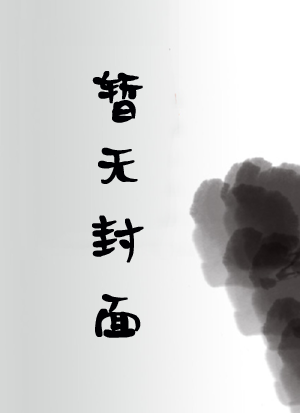第一卷:默認 番外 春天的風
“實在是抱歉,我本來不該來麻煩你們的,但我實在沒辦法了,我太着急了。”
“沒關系,應該的,我也很希望能幫得上忙。”
客廳裡,小飯桌已經被收拾幹淨了,花之盒的院長拘束地坐在沙發上,一臉慚愧。
池彎刀卻毫不在意,開門見山道:“你帶照片了嗎?最好要最近的,知道她穿着什麼衣服什麼鞋子……”
“這……”老人噎了一下,“沒有,别說最近的了,就是一年以内的都沒有,這孩子最讨厭拍照。”
“那她走的時候穿什麼衣服?”
“……也不知道,我還以為她上學呢,直到學校打電話我才知道她人不見了。”
“……”池彎刀也傻眼了,“那……照片一張都沒有嗎?”
孫院長尴尬地遞了張照片過來:“有辦學籍的證件照,也是兩年前的了,那時候還是短頭發,和現在有些不同。”
池彎刀:……
池彎刀默默接過照片看了一眼。
——眼前一亮。
她立刻就體會到老池說的“隻要你注意到她就一定不會忘”是什麼意思了。
黑漆漆的短發本該顯得乖巧,但女孩沒有表情直視鏡頭的樣子,卻隻能讓人感到鋒芒畢露的冷。
她看着鏡頭,目光好像能穿透一切,卻又不為任何人任何事停留。
明明有張漂亮極了的臉蛋,但卻散發着能吓壞同齡人的尖銳氣場。
“現階段有什麼線索嗎?比如是在哪裡失蹤的?和誰走得近?學校的監控呢?”
“沒有走得近的人,老師都一問三不知的,至于監控……”孫院長苦笑道,“她避開了所有監控,一點線索都沒留下。”
“……啊?”池彎刀再次傻了,“你的意思是,‘她’!自己避開了所有監控?還是說帶她走的人避開了所有監控啊?”
“……她自己。”孫院長鼓起勇氣與她對視,十分尴尬,又十分沉重的說,“是的,這孩子是離家出走,而且多半具有很強的反偵察意識,所以警方也非常頭疼。”
“…………”
“這是她留下的字條。”
池彎刀僵硬地接過字條,看過之後好一會兒都沒有動彈,最後發自内心的疑問道:“信号器是什麼?”
“……大概就是,一種裝置吧,我也不太懂。”孫院長一陣尬笑。
“……您到底怎麼養的這孩子。”
池彎刀笑着抓了抓頭發,然後沖老頭豎起個大拇指:“太厲害了!”
“……”老院長嘴角抽搐,最後還是沒能笑出來。
他們交流情報的時候,溫璨拿過了那張字條。
筆迹很漂亮,是和照片一樣讓人眼前一亮的突出。
上面是這樣寫的。
【原初說,我一定會找到一個百分之百愛我的人,他說等找到那個人,我的信号器就一定會有反應。
所以,為了找到那個人,我要走了,不管有多遠,就算一去不回,我也不會停下來的。
再見,别來找我,煩。】
少年對着這張字條愣了好一會兒,然後發出一聲啼笑皆非的輕哼。
他又拿起桌上的照片,燈光下少女沒有表情的直直看着他,和幾年前他在教室裡見到的那個小屁孩區别不大。
還是顯得這麼沒禮貌,讓人隻想叫她小屁孩。
“對了,還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呢。”池彎刀在問,“尋人啟事總得有個名字吧。”
“葉空,葉子的葉,天空的空。”
孫院長的回答傳到少年耳中,他不知不覺跟着重複了一遍。
“葉、空。”
兩個字,含在齒間輕吐出來,有種輕靈冰涼的韻律。
很好聽,也很好看。
·
回到玉洲。
就和在花盒時池彎刀從未洩露出半點不對那樣,同樣決絕的,她幾乎是立刻就掀起了巨大的動蕩。
溫氏集團模範夫妻鬧婚變的事瞬間席卷所有八卦頭條。
上流階層、财經圈子,乃至人人都能參與的網絡上,都被這一件事給占去了熱度。
池彎刀先是買房搬出來,然後協商離婚,被拒絕後立刻組建律師團隊向法院起訴離婚,除了内情保密外,整件事鬧得轟轟烈烈,面對一波又一波的采訪都從不動搖,從前談笑間的愛語和柔情如水汽般蒸發殆盡,任誰都能看出她的意志有多堅決。
光是為了離婚這件事她就已經忙得不可開交,應付溫榮、溫勝天、公司上下,以及媒體就已經幾乎占滿了她所有時間,然而她偏偏還能出入在學校裡繼續上課。
以前一些愛走神的學生都不由得肅然起敬,再也不敢東張西望了。
與此同時,還有幫花之盒找那個離家出走的小孩的事兒她也盡力了。
印尋人啟事,全國各個城市到處張貼,同時想辦法聯系民間找孩子的組織以及私人偵探所,總之能想到的渠道都去盡力了,然後這事兒就逐漸被淹沒在了忙碌之中。
直到一個出差的深夜突然接到玉洲警方的電話,她好一會兒才反應過來是怎麼回事。
“你說找到人了?就在玉洲?”
睡夢中的池彎刀坐起來,看了眼時間:“我現在在國外,沒辦法來接人,我叫我兒子來吧。”
“地址是?”
·
國内正是太陽落山的時候。
接到老媽電話的溫璨也同樣好一會兒才反應過來。
于是隻好拒絕了江叙一起打球的邀請,同時還推遲了一個電話會議,他舍棄了堵得正死的交通,背着包穿着球鞋,像個普通大學生一樣坐了一個小時的地鐵,又走過了兩條長長的老舊的街道,在叮鈴鈴的自行車鈴和若隐若現的蟬鳴中,少年推開了派出所斑駁模糊的玻璃門,于啪一聲亮起來的發黃電燈下,看見了一個坐在喧鬧中一動不動的側影。
風從他身後吹進去,吹動她長到肩膀的頭發,露出雪白小巧的鼻尖,和垂落的黑色睫毛。
聽到聲音時辦事大廳裡的大多數人都擡起了頭,唯獨那孩子無動于衷。
在流動的畫裡,唯獨她是一顆堅硬冰冷的頑石。
溫璨莫名看了她幾秒,才松開手,邁步走進去。
“來辦事?”
“來接人。”
面對警員的詢問,溫璨淡淡道:“一個叫葉空的,離家出走的小屁孩。”
女孩終于有反應了。
在他不動聲色又居高臨下的注視裡,女孩無聲擡頭——
一如他的想象,卻又更勝過他的想象。
溫璨從未見過能把“無動于衷”四個字诠釋得如此極緻的人。
那是全世界隻有她一個人的目光。
她看着他,看着一切,卻好像隔着玻璃在看魚。
她是世界的觀衆,觀衆席上隻有她一個人。
——
“你誰?”
觀衆終于說話了。
四周的空氣重新流動起來,嘈雜的聲音重新湧入耳中。
在這吵鬧的全是大人的辦事大廳裡,那種奇妙的感覺緩緩消散。
溫璨居高臨下看着她,心想:不過是個需要大人來領的小屁孩而已,坐在高腳椅上腿都夠不着地的小短腿。
“我叫溫璨,溫柔的溫,璀璨的璨。”
高挑挺拔的美少年背着包彎下腰來,視線與少女的平齊,同時擡手毫不客氣地蓋住了她的腦袋:“從現在開始,我就是你的監管人了。”
又有人推開大門。
傍晚的風和盛大的餘晖一起湧入人聲嘈雜的辦事大廳。
來來去去的人流中,二十歲的少年和十四歲的少女無聲對視,都在彼此瞳孔裡看見了清晰的自己。
下一秒,少女毫不猶豫地打開了頭頂那隻手,發出啪的一聲——